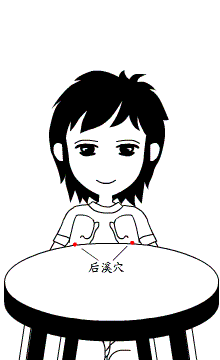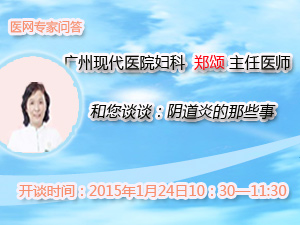关爱肿瘤患者远比治疗重要
医网摘要: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面临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曾忧心如焚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的日趋紊乱的年代”。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描绘了当时肿瘤治疗的窘境。
“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这是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
对肿瘤病人而言,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为此,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提出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的理念。他表示,这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编 者
1 “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
几年前,也是在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我到一个城市参加抗癌大会。在前往会场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肿瘤医院,便不无幽怨地说:“这条路我太熟了,我母亲就在肿瘤医院治了好几年,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拉的‘饥荒’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把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带到了当天的会议上,引起了与会者的议论和深思。
第21届世界抗癌联盟大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预防可以预防的肿瘤,治疗可以治疗的患者,通过体系加以实现。”这一口号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不要在肿瘤病人身上做得太多”。
“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这是医圣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事实上,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患者,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直接使患者对当下种种医疗行为产生“恐惧感”。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生,却仍然不得不花费精力,执著地识别、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日益发达的互联网也常常传递出肿瘤病人的无奈。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几年前查出患有肿瘤,他临终前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说:“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每天,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尽头了,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半年了,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当然,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实际上,过度治疗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和主流。毕竟,遏制过度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根基在于改变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理念,而改变理念比弥补硬件上的缺陷要复杂得多。
2 “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
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曾直言,“过度检查和医疗是美国医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他们预言,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到2019年,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将达到4.3万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9.3%。尽管癌症医疗护理的开支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它的成本上升非常快,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病人群的增加,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技术至上”盛行,医学与人渐行渐远,技术和市场“绑架”了医学。韩启德院士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到1万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减轻了,但调查显示,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2010年4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病人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该公司印发的药品宣传彩页有一个醒目且诱人的标题——“肿瘤治疗从此走向新时代”。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要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
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就像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盖博·维奇说的,“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
3 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
今天之所以提出肿瘤的“适宜治疗”理念,还因为在对过度医疗一边倒的诟病中,与过度治疗同样严重存在的“治疗不足”和“治疗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对“身”处置过度,对“心、灵、社”关注不足。
从医疗资源的分配上,现行的主流医疗模式和医疗制度,把医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固定”在住院的“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身上,使肿瘤医生实际上面对的只是占5%~10%,甚至更低比例的“小众”患者群体。对已完成抗肿瘤治疗的潜在治愈者、带瘤生存者和处于疾病缓解、观察期的那些“没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失医者”群体。肿瘤医生该如何承担起这个潜在的医学责任?这在国内外都鲜有成熟经验可循,也无政策制度为据。
肿瘤病因机体内外环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样性、肿瘤病理形态的异质性、手术和放疗的局限性、药物治疗中的多药耐药性、患者心理素质和社会状况及基础疾病的复杂性、医生观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等,常使肿瘤治疗显得无定力、无层次——或者“一条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疗不止”;或者左顾右盼,拿捏不准患者是否获益的“治疗拐点”、治疗重点应否转移;或者干脆放任,将其边缘化而无人问津。
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时代”。这句话再贴切不过地描述了当前肿瘤治疗的窘境。
显然,要走出这种窘境,首先应当明确治疗的目标,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肿瘤医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一位患者在得知自己“晚期肿瘤”诊断的第二天对我说:“过去的24小时是浓缩了我生命的一天——我回顾了一生,以倒计时的方式规划了未来。我对即将开始的治疗充满期待,希望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我也做好了不测的准备。”
4 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但目标不能紊乱
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对生命、对患者、对实践的深刻认知和尊重,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坚定对所有肿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过度,进行“适宜治疗”的信念。
我们常说,肿瘤医生有两大任务——延长患者的生命和减轻患者的痛苦。但这似乎又是不够的,医生的良知和职业素养应当表现在不只是简单地让患者生存,更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在延续生命和肉体无痛苦之上,还应有一种更高的追求,那就是人类本能的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质量,即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
社会对肿瘤医生的职业要求是:以善良悯人之心,给患者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肩负起做幸福感的传递者和幸福梦的“圆梦人”的责任,锻造并赋予一个生命以崭新的面貌,哪怕这个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这也应该成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发自内心地对生命和对患者的尊重。因为,当我们仅以生命的长度衡量患者的生命时,这个生命是躺着的线段;当我们关注到患者肉体无痛苦时,这个生命是一个可见的平面;只有我们关注到患者的方方面面,关注到他生活的“幸福度”时,这个生命才能站立起来,成为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肿瘤治疗尤其如此。当前,对中晚期肿瘤的治疗手段繁多,良莠难分,效果迥异。在如此“乱世”之中,医生的头脑应保持冷静——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但目标不能紊乱。“帮助病人幸福地活着”应当成为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十几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肿瘤的不同症状、体征和临床特点,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治疗的实际效果,制定了许多治疗规范、指南和共识。这些带有指导意义的医疗文件对规范并实现肿瘤的适度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完善。
对肿瘤“适宜治疗”的追求,就在于让肿瘤病人即便行将辞世,也能不留遗憾地对这个世界和他们的亲人说一声:“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也对自己的医生满意。”
本文来源: http://www.ew86.com/cancer/20150918/1174476.html
对肿瘤病人而言,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为此,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提出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的理念。他表示,这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编 者
1 “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
几年前,也是在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我到一个城市参加抗癌大会。在前往会场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肿瘤医院,便不无幽怨地说:“这条路我太熟了,我母亲就在肿瘤医院治了好几年,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拉的‘饥荒’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把出租车司机的这番话带到了当天的会议上,引起了与会者的议论和深思。
第21届世界抗癌联盟大会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预防可以预防的肿瘤,治疗可以治疗的患者,通过体系加以实现。”这一口号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不要在肿瘤病人身上做得太多”。
“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太多”。这是医圣希波克拉底给后世医生留下的警世恒言。事实上,过度医疗不仅伤害了患者,对医生职业的尊严和本应得到的社会尊重与信任也造成了重创,直接使患者对当下种种医疗行为产生“恐惧感”。他们在面临尊严恐惧、社交恐惧、账单恐惧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就医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生,却仍然不得不花费精力,执著地识别、规避现行落后的医疗理念可能给自己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日益发达的互联网也常常传递出肿瘤病人的无奈。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几年前查出患有肿瘤,他临终前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说:“这些年,我算是找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了。每天,我都要和来自医院内外的五花八门的忽悠‘斗智斗勇’。就要走到尽头了,这样的生活却不值得留恋。”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从诊断为肺癌那天起,半年了,我壮硕的父亲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手术,后放疗、化疗。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疼痛、失眠很快把父亲折腾得脱了形。医生却总是告诉我们,瘤子有缩小,治疗有效果,‘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当然,如果把当前肿瘤治疗的弊端,完全归结为医生在利益驱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过度治疗,也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偏颇解读。实际上,过度治疗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和主流。毕竟,遏制过度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根基在于改变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的理念,而改变理念比弥补硬件上的缺陷要复杂得多。
2 “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
何谓过度医疗?美国心脏病学会给出的定义是: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曾直言,“过度检查和医疗是美国医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他们预言,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到2019年,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将达到4.3万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9.3%。尽管癌症医疗护理的开支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大,但它的成本上升非常快,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病人群的增加,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当前医学技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过度使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技术至上”盛行,医学与人渐行渐远,技术和市场“绑架”了医学。韩启德院士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运用最高端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到1万元;胃癌的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虽然诊断的精度提高了,化疗的副作用减轻了,但调查显示,胃癌5年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2010年4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一种肿瘤生物治疗药物,临床应用的统计学结果显示其只能延长病人4.1个月的生存寿命,却要付出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高昂代价。该公司印发的药品宣传彩页有一个醒目且诱人的标题——“肿瘤治疗从此走向新时代”。难怪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研究小组要警告说:“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创造供应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
我国卫生主管部门也曾指出,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极大地增加了全民医疗支出,普遍存在着“人生最后一年甚至一个月,花掉一生80%医药费”的状况。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广大群众对医学的误解、医务人员对高科技的盲目崇拜,全方位地增强了过度医疗的吸引力。就像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盖博·维奇说的,“过度医疗要挑战它太难,支持它又太容易”。
3 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
今天之所以提出肿瘤的“适宜治疗”理念,还因为在对过度医疗一边倒的诟病中,与过度治疗同样严重存在的“治疗不足”和“治疗缺位”被忽略了。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是:在抗癌过度的同时,对姑息支持、生命关怀远远不足;对“身”处置过度,对“心、灵、社”关注不足。
从医疗资源的分配上,现行的主流医疗模式和医疗制度,把医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固定”在住院的“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身上,使肿瘤医生实际上面对的只是占5%~10%,甚至更低比例的“小众”患者群体。对已完成抗肿瘤治疗的潜在治愈者、带瘤生存者和处于疾病缓解、观察期的那些“没有治疗价值”的肿瘤患者,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失医者”群体。肿瘤医生该如何承担起这个潜在的医学责任?这在国内外都鲜有成熟经验可循,也无政策制度为据。
肿瘤病因机体内外环境的多元性、癌基因的多样性、肿瘤病理形态的异质性、手术和放疗的局限性、药物治疗中的多药耐药性、患者心理素质和社会状况及基础疾病的复杂性、医生观念的片面性以至知识结构的单一性等,常使肿瘤治疗显得无定力、无层次——或者“一条道走到黑”,“生命不息,抗癌治疗不止”;或者左顾右盼,拿捏不准患者是否获益的“治疗拐点”、治疗重点应否转移;或者干脆放任,将其边缘化而无人问津。
上世纪50年代初,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这是一个手段日臻完善,但目标日趋紊乱的时代”。这句话再贴切不过地描述了当前肿瘤治疗的窘境。
显然,要走出这种窘境,首先应当明确治疗的目标,而患者的需要和期盼就是肿瘤医生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一位患者在得知自己“晚期肿瘤”诊断的第二天对我说:“过去的24小时是浓缩了我生命的一天——我回顾了一生,以倒计时的方式规划了未来。我对即将开始的治疗充满期待,希望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我也做好了不测的准备。”
4 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但目标不能紊乱
对肿瘤进行“适宜治疗”固然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肿瘤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患者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对生命、对患者、对实践的深刻认知和尊重,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坚定对所有肿瘤患者既不缺位也不过度,进行“适宜治疗”的信念。
我们常说,肿瘤医生有两大任务——延长患者的生命和减轻患者的痛苦。但这似乎又是不够的,医生的良知和职业素养应当表现在不只是简单地让患者生存,更要追问这是何种生存。在延续生命和肉体无痛苦之上,还应有一种更高的追求,那就是人类本能的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质量,即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
社会对肿瘤医生的职业要求是:以善良悯人之心,给患者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肩负起做幸福感的传递者和幸福梦的“圆梦人”的责任,锻造并赋予一个生命以崭新的面貌,哪怕这个生命将不久于人世。
这也应该成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发自内心地对生命和对患者的尊重。因为,当我们仅以生命的长度衡量患者的生命时,这个生命是躺着的线段;当我们关注到患者肉体无痛苦时,这个生命是一个可见的平面;只有我们关注到患者的方方面面,关注到他生活的“幸福度”时,这个生命才能站立起来,成为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肿瘤治疗尤其如此。当前,对中晚期肿瘤的治疗手段繁多,良莠难分,效果迥异。在如此“乱世”之中,医生的头脑应保持冷静——肿瘤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虽然难以预期,但目标不能紊乱。“帮助病人幸福地活着”应当成为我们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十几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肿瘤的不同症状、体征和临床特点,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治疗的实际效果,制定了许多治疗规范、指南和共识。这些带有指导意义的医疗文件对规范并实现肿瘤的适度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完善。
对肿瘤“适宜治疗”的追求,就在于让肿瘤病人即便行将辞世,也能不留遗憾地对这个世界和他们的亲人说一声:“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也对自己的医生满意。”
本文来源: http://www.ew86.com/cancer/20150918/1174476.html